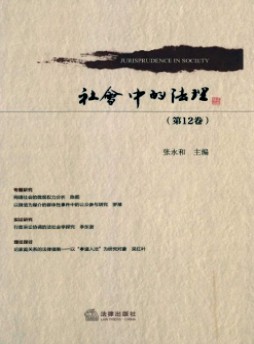小義在社會中尋求自由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小義在社會中尋求自由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格林認為自由不是原子式個體的占有物,而是社會主體自我實現和增進社會共同善的能力。自由只有在社會中,通過社會和個人的相互作用才能實現。社會可以且有義務增進個人自由和社會共同善,而個人有權也有責任參與社會體制的建設。但個人價值依然是自由的最終價值標準。在協調個人和社會的關系中,格林把自由和民主結合起來,變早期的消極自由觀為積極自由觀,既推進了自由主義的演進,又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關系。
關鍵詞:格林;積極自由;個人;社會
在思想史上,對自由的理解,始終與一個核心問題聯系在一起,即如何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劃出一個行動的范圍,既能保證個人的自由行動,又能保護社會整體的權益。近代早期自由主義理論的解決思路,通常是賦予個人絕對的優先地位,使之擁有絕對的自然權利,他人和社會都不能干擾這些權利的行使。社會被看作是個人的集合體,其福利只不過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這樣一來,自由被理解為個人私人的占有物,他人和社會的存在是外在于個人自由的,是實現個人價值這一目的的手段,甚至成為干擾個人自由的來源。個人和社會成了一種對立的關系。這種自由理論及其代表和促成的社會實踐,必然造成個人自由的張揚,而忽視甚至損害社會福利和自由。一部分人或階級的自由以犧牲其他人或階級的自由為代價而獲得,社會正義和整體福利受到損害,這反過來又限制了個人自由的進一步發展。這種情況在19世紀后半期的英國表現得尤為明顯。傳統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導致了工業生活中的貧困和社會生活的墮落——主要表現為赤貧的無產階級的產生和對社會生活苦難的理性的冷漠,這種狀況的存在破壞了個人的自我實現。為改變這種狀態,英國社會進行各種立法,卻因對個人的干預而被認為是對自由的侵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托馬斯·希爾·格林(ThomasHillGreen,1836-1882)引進了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重新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強調兩者之間互為前提,相互促進的關系,主張社會可以且有義務為促進個人自由而積極行動,而個人也應參加到社會體制建設當中,從而變早期的消極自由觀為現代強調社會正義和個人責任的積極自由觀,把自由和民主結合起來,推進了自由概念的演進。
一
對自由的理解,總是同人性觀聯系在一起的。早期的自由主義者把人看作是原子式的功利人,這使得他們把自由看作是原子式的功利人的私人占有物。在大部分契約論者看來,個人最初是孤立于社會的個體,生活在自然狀態中,擁有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只是由于自然狀態之中存在諸種不便,才訂立了所有人與所有人的契約,進入政治社會。稍晚一些的功利主義者盡管沒有采用契約論的概念,但仍可以看作是這種觀點的繼承者。他們強調個人對快樂及實現快樂的手段的追求,進一步強化了原子式的功利人的人性觀。在此基礎上,自由被看作是個人所擁有的一系列社會不得干預的天賦權利,其根本屬性在于沒有外在的干涉。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寫到,“自由……指的是沒有……外界障礙”[1](p.162),自由人就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辦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礙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1](p.163)
格林反對原子式的功利人的人性觀。他指出,自然狀態在歷史上不存在,在邏輯上也不成立。從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出發,格林認為人就其本性而言乃是一種生活在社會中的道德存在。他是永恒意識(即上帝)在動物有機體中的再生,而非受欲望驅使的動物。他有自我意識,能夠把自我同一系列生活過程中所產生的需要區分開來,不是簡單地滿足于欲望的滿足,而是追求自我實現,追求與上帝的融合,從而成為一種永恒意識。他的自我實現或者說真善,只能存在于“使可能的自我成為現實”的過程中[2](p.224),而“無法在對快樂的占有中獲得,也無法在對實現快樂的手段的占有中獲得”[3](sec.246)。由于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和共同的目的,并且每一個個體都是有限的,他無法單靠自己而成為永恒意識,必須在與他人及人類社會的關系之善中實現它,所以,個人的真善必然是一種共同善,他人的善是個人的善的組成部分,他人的善和社會的善的實現是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這一觀念不承認個人的善和他人的善的區分。”[3](sec.235)因此,人本質上是一種追求共同善的道德存在,他的自我實現或者說自由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獲得。
基于這一認識,格林指出,自由不是僅僅免于約束或強迫,不是僅僅按我們的喜好去行事,而不管這些喜好是什么[4](p.370)。因為僅僅沒有外在干涉并不能夠確保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它可能帶來的后果就是很多人是不自由的,有些人以犧牲其他人的自由獲得自由。例如,資產階級的自由建立在無產階級的不自由之上。工人們被迫“在不利于健康、體面的住所和教育”[4](p.377)之下工作和生活,致使他們最終被剝奪了“自我發展的真正機會”[3](sec.245)。這種剝奪使得他們從社會中完全自主的公民當中被排除出來,他們被關在“自由的社會生活”[3](sec.250)之外,被剝奪了“公民社會成員的資格”[3](sec.245)。這“妨礙了整體自由,削弱了我們……最大程度發展自己的能力”[4](p.373),從而使得自由被一部分人或階級以犧牲他人的自由為代價獲得,成為剝削的借口。因此,僅僅排除強迫,僅僅使一個人能夠做他想做的事情,這本身對真正的自由毫無貢獻[4](p.371)。與此同時,格林也指出,沒有外在的強制是自由的必要條件,“在出于被迫行為的人們中間無自由可言”[4](p.371)。人不能夠被強制自由,因為真正的自由在于做某人該做的,即道德地行動,而道德行動是不可以通過強迫行動獲得的,它們依賴于行動的動機,動機是無法通過強迫獲得的。對某人的強制只是用來防止他對他人自由的侵犯。
在格林看來,自由乃是積極的社會主體擁有的自我完善和實現共同善的能力。他寫道:“自由是一種做或享有某些值得做或享有的事物的積極的力量或能力,是一種我們可以與其他人共同做或享有的東西”[4](p.371),“當我們用一個社會在自由方面的發展來衡量它的進步時,我們是以增進社會的善的那些能力的不斷發展和越來越多的運用來進行衡量的,并且我們相信每個社會成員都被賦予了社會的善。簡而言之,是用作為整體的公民體系擁有較大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地、最好地完善自己這一標準來衡量。”[4](p.371)
因此,他的自由概念通過三種方式與早期自由主義的自由理念區別開來。首先,自由是與道德聯系在一起的。它是人們做值得做的事情的能力。其次,自由與平等的機會緊密相關。“每個人都應該總是被當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3](sec.267),任何人或階級都不能以犧牲他人的自由為代價來獲得自由[4](p.371)。所有人都應該擁有自我實現的機會,能夠分享社會進步帶來的福利,并參與到社會進程當中來,成為社會生活的主人。這為自由提供社會正義,使其獲得合法性。最后,自由始終和能力聯系在一起。自由不只是意味著法律上的自由,而是按照現有條件發展人的能力的實際可能性,是個人真正增加分享社會有價值事物的權力,并且是為了共同利益擴大做出貢獻的能力。僅僅是沒有外在的強制,不足以使人自由。他還必須免于內在的障礙,具有理性,能夠避免錯誤的自我意識,在善的目標中實現自我。他還必須考慮到所有與其自我完善有關的人的完善。他也需要有價值的可能性可供選擇,為此必須被賦予實現個人完善所必需的基本福利。因此,社會應該為個人提供實現自由所必需的條件。正是這些特征,決定了格林所提倡的自由必然與社會緊密相關,它只有在社會中,通過社會機構的促進才能得以實現。
二
既然自由是社會主體擁有的實現社會共同善的能力,那么,它就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實現。格林指出,在某種意義上,沒有人能夠如他所喜歡的那般,隨心所欲地像一個到處游蕩的野蠻人一樣行事。雖然他不是人的奴隸,沒有主人,因此沒有人可以禁止他,但我們并不認為他是自由的,因為野蠻人的自由不是力量,而是虛弱。雖然社會對他沒有任何限制,但他卻是自然的奴隸,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強制。因而,最高貴的野蠻人擁有的實際力量也無法與守法國家的最卑微公民相比。他除了服從于社會的約束之外,別無其他途徑擺脫自然必然性的強迫。因此,服從乃是通向真正自由的第一步,因為這一步導向人被賦予的才能的完全運用[4](p.371)。
在格林看來,個人是通過社會才獲得自我實現和自由所必需的權利的。早期的自由主義者認為,權利是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或者因其有助于獲得最大快樂的功用而獲得合法性。它更多地被看作是個人的所有物,用以反對社會對個人的干預。格林認為,不存在先于社會的天賦權利,快樂也不是權利所服務的目的。權利是因為其所服務的目的而具有合理性的,這一目的就是社會的共同福利[5](sec.38)。權利始終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它是個人的要求,產生于人的理性本性,想要自由地運用自己的某些能力;另一方面,它是社會對這種要求的承認,是社會賦予個人實施這一要求的權力[5](sec.139)。當個人意識到為了他自己道德能力的發展和社會的共同善,他必須擁有某項權利時,就向社會要求獲得這項權利,而其他社會成員承認為了他和社會的善的實現,應該賦予他這一權利。某項權利被賦予個人的唯一理由,就是因為這樣有助于社會共同福利的發展[5](sec.142)。一旦社會的良知認識到某一項權利實行的結果會導致對個人自由和社會共同福利的損害,他們就可以要求對這一權利進行調整。因此,他永遠是作為社會的成員獲得權利的,正是這一身份確保了他獲得這些權利,個人的權利只能來自社會。不存在先于社會的天賦的或自然的權利,更沒有反對社會的自然權利[5](sec.141)。說一項權利是自然的,是指它對于道德能力的實踐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它,人就不成其為人[5](sec.30)。總之,權利不是個人用來反對社會的武器,而是社會賦予作為社會成員的個體實現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的能力,個人的權利來源于社會。
格林認為,國家作為一種高級的政治社會,可以通過對權利體系的維護和協調,推進共同善。國家“對其成員而言是社會的社會,在其中他們對彼此的所有要求都被相互調整了”[5](sec.141),它是“推動共同善的公共機構”[5](sec.124),不再被看作一種不可避免的罪惡,一個消極的“守夜人”,其目的和職能也不再僅限于保護私人財產和人身安全,保障社會秩序。它通過法律維護和協調道德能力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權利體系,因其所服務的目的成為一個道德的實體,為這一道德目標所驅使而生氣盎然。雖然公民并不是從它那里取得其道德觀的,但是他們卻從它那里取得了作為實現道德的條件的種種權利,因而通過它公民才是有道德的。它在個人力求做“值得做的事情”時,拆除設置在他前面的障礙物。為了維持種種條件和拆除種種障礙,它積極干預凡屬傾向于破壞有關條件或設置障礙的事情。它動用武力以擊退破壞自由的力量,為了自決地走向共同的善而解放人類的能力的目的而積極行動。作為一系列公認的權利的維護者,國家及其法律理應受到尊重。因此,除非從國家利益出發,否則,不能有違反法律的權利[5](sec.142)。不能為了一項權利而冒險反抗法律,因為法律所維護的是基于同樣理由的一整套權利體系。只有當這項權利為社會公認,同時又受到壓制,并且反抗不會帶來危險時,才是理性的。
格林主張,為了維護和協調權利體系,增進個人自由和社會共同福利,國家有權且有義務對那些給社會帶來麻煩的個人自由進行干預。
國家可以對契約自由進行干涉。格林指出,“契約自由,以及各種按照人們自己意愿行事的諸種自由,只有在充當目的的手段時才是有價值的,這一目的就是我在積極意義上所主張的自由;換句話說,是所有人平等地為促進共同善而擁有的能力的解放。”[4](p.372)當饑餓的工人們迫于生存壓力,簽訂不利于健康和安全的勞動合同,被剝奪了自我實現的機會,使促進社會共同善的能力受到損害時,國家有權通過法律加以禁止。又如,愛爾蘭的農民除了土地之外別無其他謀生手段,為了維持生存,容忍地主在簽訂土地契約時無理地提高地租,縮短租期。他們在同地主簽訂合同時,并不比饑餓的工人向提供工作的老板尋求好薪水的自由多。這時候契約自由徒有其名[4](p.382)。這樣的契約,“注定使契約自由——這一社會的保障——的尊嚴散失”[4](p.382)。因此,格林主張對這些契約自由加以限制。他寫道:“捍衛契約自由,毫無疑問是政府的主要工作。但是,同樣重要的是,反對契約變成對簽約的一方不利,以免其非但不保障自由,反而變成虛偽的壓迫的工具。”[4](p.382)
國家還可以對財產權的自由進行干預,以保證財富為社會的共同利益服務。他寫道,“人不僅是財產的人。財產制度只有在作為工具,用以促進整個社會所有人才能的自由的行使時,才是合理的。當一個階級被完全從自由中排除掉時,不可能存在財產權。”[4](p.372)他認為,當時英國不良的土地授與制度,使得土地一成不變地傳給長子,掌握在那些個人和家庭負擔過重的人手中,無法得到有效的改良,土地只能產出實際地力的一半;也徹底阻斷了土地買賣,阻止了擁有小塊土地的自耕農的產生,而他們是社會秩序的主要依靠。這些都違反了公共利益,法律應該阻止這種妨礙土地分配和改進的安排[4](pp.378-9)。另外,對那些不把土地用于農業,而是為了玩樂把其變成樹林的地主的權力也應該加以禁止[4](pp.379-80)。
出于公眾利益的考慮,酒類買賣的自由也應該受到限制。格林把酗酒的習慣同無產階級的悲慘狀況聯系起來,認為它是無產階級自我意識不足的表現,也是造成他們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主張限制甚至取消酒類買賣。他寫道:“如果一種特定商品的買賣,允許其自由進行的通常結果是在更高層次上遠離自由,損壞人們完善自身的共同力量,那么,無權要求這種權利。”[4](p.383)過度的飲酒意味著對他人的健康、錢財、能力的傷害。一個家長酗酒,通常意味著這個家庭所有成員的貧窮和墮落。街頭的酒店的存在,則往往意味著這條街上大量的家長酗酒。這會對社會成員自由的改善造成損害[4](p.384)。因此,社會可以對酒類的買賣加以更進一步的限制[4](p.384)。“等待是非常危險的”[4](p.385),因為酒類貿易中的既得利益會變得越來越強,受影響的人也越來越多。
義務教育也是國家干預的范圍。格林指出,在現代社會,個人如果沒有掌握相當的技藝和知識,就如同失去肢體或者軀體受損一般,沒有生活能力,不能自由地發展他的能力,教育“理所當然地處于政府的范圍之內”[4](p.374)。
針對國家的干預干涉了那些受到幫助的公民的自立的指責,格林認為這混淆了中央集權和限制那些給社會帶來麻煩的自由的立法[4](pp.374-5)。國家干預不需要干涉這些公民的自立,因為“它不過要求他們做他們本來要為自己做的事”[4](p.375),法律只不過是他們的一個得力的朋友,懷著由衷的祝愿,幫助他們達成自己難以完成的事。他們從這些方面解脫出來的責任,會相應地在其它地方承擔起來。格林提醒反對社會立法的人,“我們必須按照我們所遇見的人們的情況來對待他們”[4](p.375),工業生產中勞動者的情況悲慘,如果不進行干預,這種情況就會延續下去,并且日趨嚴重。因此,法律必須出面干預,而且要這樣干預若干代[4](p.377)。